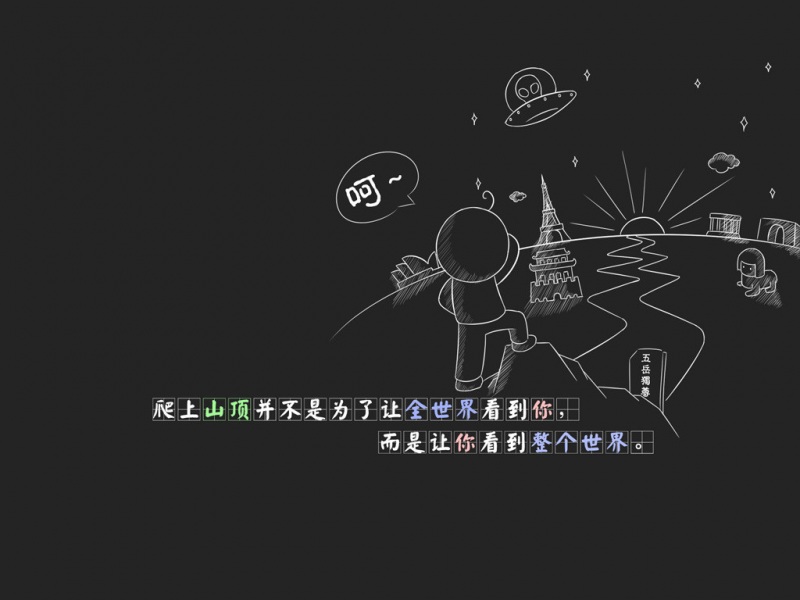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由伊利卡与贾高沙合作编剧,是根据贝拉斯特(1859-1931)的同名戏剧,而这部戏剧又根据约翰·络德·朗(l861-1927)的小说而作。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谱曲,是普契尼三大歌剧之一。1904年2月17日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首次公演。修订版于1904 年5月28日,在布雷斯加大剧院首演。
故事以二十世纪初日本长崎为背景,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经婚姻掮客介绍,娶了年仅十五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即蝴蝶夫人)为妻,但这位美国佬对此桩婚事则抱持游戏态度,新婚不久后即随舰队返回美国,而巧巧桑仍不改初衷,终日痴心等待,结果竟换来丈夫的恶意拋弃。待三年后平克顿返回日本时,则带来了真正的美国妻子,并且要求带走与蝴蝶夫人所生的小孩,蝴蝶夫人应允“丈夫”的请求,而自己却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场婚姻悲剧。
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扉页上印上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们不能表达他们自己,他们只能由别人来代为表达(represent,即代表)。”马克思这句话本来是用来讲阶级差别的,这个“他们”说的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被剥夺了话语权;赛义德则把这句话套用来形容东方人在西方文学中的处境。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对歌剧大师普契尼的《蝴蝶夫人》(1904年)和《图兰朵》(1924年)都很适用,因为这两个剧中的东方人完全是普契尼这个意大利白人创作的,其间没有一点东方人的参与。具体而言,应该说这个批评对《图兰朵》非常贴切,该剧中那个杀人如麻的中国公主本来就是荒唐的编造,而张艺谋等中国人用一面“西方经典”的大旗来包装所谓的“中国故事”,借用他人胡乱的“代表”来表达自己,更是荒唐之至。从赛义德理论推演出来的后殖民戏剧理论认为:戏剧再现的过程本身就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把一个族群的文化价值强加到另一个族群的成员头上:一边说要表现他们的不同特色,一边却在把他们漫画化;一边说要庆祝他们存在的价值,一边却在抹杀他们的存在。
《蝴蝶夫人》和《图兰朵》的主人公都是异国姻缘中的东方女子,恰恰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图兰朵磨刀霍霍,发誓要杀尽所有看上她的男人;蝴蝶夫人却忠心耿耿,默默地为一个负心的郎君而自杀身亡。当然,这两个女人都不是东方女子的榜样,但蝴蝶夫人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在审美的意义上,《蝴蝶夫人》在20世纪世界各地舞台上取得了罕见的持久成功;在现实或者说社会学的层面上,蝴蝶夫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西方的左派——尤其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还有那些生活在白人世界里的亚洲人后裔——把蝴蝶夫人说成是逆来顺受的“模范少数民族”亚洲人形象的始作俑者——一个负面的原型。在当代美国,对于西方人塑造的东方人形象的一个公认的判断是:“一百年来在美国代表亚洲人的流行形象从来没有超越过这样一个层次——给它最好的评价也就是脸谱化。”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蝴蝶夫人。但讽刺的是,《蝴蝶夫人》的演出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减少,反而还催生出一系列以之为原型的衍生作品。于是批评家更加批评说,蝴蝶夫人流毒深广,模仿者众多,已经成了脸谱化的亚洲女子的代名词。这样的批评实在不大公平,应该说,有人模仿是因为这个故事有典型意义,怎么能怪原作者呢?其实二者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同于《图兰朵》中凭空捏造的东方人形象,《蝴蝶夫人》中的日本女性是从许多真实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
和《图兰朵》相似的是,以歌剧闻名于世的《蝴蝶夫人》原来也是一个话剧,而在话剧之前,最早的故事原型也来自书中;但《蝴蝶夫人》的书——话剧——歌剧的三级跳比《图兰朵》紧凑得多,前后总共才(《图兰朵》从书到歌剧花了200多年)。更重要的是,这个跨文化戏剧的创作过程整个比《图兰朵》晚很多,是在东西方之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交流,西方艺术家对东方有了较为切实的了解之后。日本于1854年在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的大炮面前签下第一个打开国门的条约,1868年宣布明治维新,对西方世界全面开放,1887年一本描写日本人的法文小说《菊子夫人》问世,1889年英译本出版。小说的作者皮埃尔·洛蒂是个法国海军军官,从小爱海,其海上生涯长达42年,遍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许多国家,他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游记的味道很浓,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书中作为第一手资料记录下来的异国情调已经很可以吸引没有机会亲自去猎奇的欧美读者。
《菊子夫人》大致上也是这样,几乎是洛蒂自己和一个日本女人同居两三个月的日记节选。这个日本女人菊子并不是后来的《蝴蝶夫人》中那样的妻子,也不是女朋友,也不能算是妓女,而是介乎三者之间的短期合约夫人,时间以军舰在港口驻扎的时间为限。虽然主人公“我”说到他们的关系时用的词是“结婚”,他们的关系事实上是租赁,这在当时的日本是合法的。菊子夫人和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蝴蝶夫人这一悲剧形象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差别,基本上是个轻喜剧的形象,根本不可能为那个白人男人而要死要活,他们一开始就说好了时间和价钱,知道他到时候要走的。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笔也是发生在“我”离开以后。那时候“我”倒“感受到一种短暂的悲哀”,开始当他再次回房间去取一件小行李时,还没进门就意外地听到了菊子的歌声:歌声是快乐的!我狼狈不堪,十分扫兴,几乎后悔又回来这么一趟。
地上,摊着所有我昨晚按协议给她的那些美丽的皮阿斯特,她正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能,捻摸、翻弄它们,将它们往地上掷,拿一柄行家的小锤,使它们在他身边发出丁丁声,一面唱着不知什么鸟儿的浪漫曲,大概使她兴之所至随便哼出来的。
这个菊子无情无义只要钱,上一任“丈夫”还没走远,已经在做准备接待下一任,这恰好证实了头天晚上“我”已经理性地做过的判断:“我努力使这次开拔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使自己动动感情,可惜收效甚微。这日本,如同当地那些小个子好男人和好女人,肯定缺乏不知什么素质,人们可以暂时拿他们寻开心,却毫不依恋他们。”
和以后广为留传的蝴蝶夫人的形象相比,菊子夫人并不是一个十分“正面”的形象,对她的描写明显地反映出白种男人居高临下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偏见直到现在还很常见,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刚刚获得美国电影“金球奖”的美国片《迷失东京》,片中用两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日本,个个都滑稽可笑,个个都让我想起当年洛蒂眼里的菊子夫人。虽然人们并不能否认洛蒂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洛蒂于1885年在长崎驻扎期间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像菊子这样从乡下来到开放港口挣外国男人钱的歌伎当时也确实不少;然而在那时候,就是许多西方人也觉得这个日本小女人不够“典型”,对于他们自明治维新以后接触了日本文化所刚刚产生的浪漫热情有点泼冷水的味道。
西方人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和它给人的神秘感很有关系。日本是远东最远的国度,开放得比中国还要晚(中国在1840年就和英国打了一场鸦片战争),但其开放却是用的和平的方式,而且一旦开放就很彻底。日本的小巧玲珑的建筑、诗歌(俳句)、戏剧(能剧)、工艺品,甚至包括他们人的体型,都使得西方人眼界大开。对于亲身在日本住过的洛蒂来说,他们的用具都像是“过家家”的东西,他们的人“还算小巧,由于长得古怪,手很细柔,脚也纤巧,可是从总体说来,很丑陋,而且矮小得可笑;神态像古董架上的小摆设,像南美洲的狨猴,像……我也说不上像什么……”然而在欧美的文艺圈里,“日本主义(Japonisme)却成了一时的时尚,法国人马奈的印象派画、爱尔兰人叶芝的仿能诗剧和美国出身的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等等都成了当时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热门话题。而这些和精明的菊子夫人的形象放到一起来看,显然很不协调。
尽管如此,《菊子夫人》还是于1893年被安德列·麦色杰搬上舞台变成了歌剧,那是因为西方对日本题材的兴趣实在太强烈了,而当时在西方能找到的日本故事又实在太少。这个歌剧和后来《蝴蝶夫人》的成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了。在该剧演出的同时,其他西方艺术家也在积极寻找更适合他们需要的日本形象。这时候又一个了解日本的跨文化作家出现了,他叫拉夫卡蒂欧·赫恩,生长在爱尔兰,19岁移居美国,后来当了记者,40岁上去了日本,以后一直住在那里教书写作,还娶了日本妻子生了孩子,变成了日本公民,写了好些关于日本的英文书和小说,向西方人介绍他所欣赏的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
短篇小说《哈茹》(1896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日本的旧式传统下教养出来的女子哈茹,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忌妒、悲伤和愤怒,但最后终于因为发现丈夫不忠而悲愤死去。这位日本女性比菊子夫人更像是后来的蝴蝶夫人的原型。在赫恩的另一篇小说《红色婚礼》(1894年)中,他描写了东方的殉情自杀的仪式。“东方的自杀不是源自盲目的狂躁的痛苦,也不仅仅是一种冷静和技术性的自杀,这是一种祭仪。”同样的仪式后来成了《蝴蝶夫人》中高潮时的关键情节。
在赫恩早期关于日本的作品中出现的多是比菊子夫人更为可爱的形象,这也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他自己的形象一点也不吸引人,个子很矮,一只眼睛瞎了,而且明显地凹下去,另一只又凸出来。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和自己同种的白种女人,在美国娶的第一个妻子是个黑人,在日本娶了日本人。他在日本感觉比在美国好得多,因此更愿意向他的同胞介绍日本好的一面,特别是日本文化中传统的一面,诸如礼貌、温和、忠义、敬老等等,写日本女性时也强调她们的优雅、迷人、感性等方面,恰恰和菊子夫人相反,而这些特征正是当时迷恋于日本文化的异国情调的欧美人士更喜欢的。
1898年,第一篇名为《蝴蝶夫人》的文艺作品发表在美国《世纪杂志》上,这是一个短篇小说,讲的也是发生在长崎的一个白种军人和一个日本歌伎之间的婚姻。小说的作者是美国人约翰·路德·郎,他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但他的姐姐欧文·考瑞尔太太嫁给了一个派驻日本的传教士,对日本十分了解,经常给郎讲日本的故事。虽然小说《蝴蝶夫人》从《菊子夫人》那里得到了很多素材,但它的主人公的性格和故事的结局完全不一样,郎在这里揉进了一个当时在长崎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一个日本歌伎给一个英国商人生了个儿子,英国人把儿子拿走放到长崎,请郎的外甥代为教育。歌伎试图自杀但被救起,后来在东京住到1899年正常去世——这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蝴蝶夫人。
小说《蝴蝶夫人》把男主角的形象也颠倒了过来,现在他不再是一个风趣迷人博学能干的法国海军舰长,而是一个头脑简单却又极端自私的美国中尉;他不再是履行合约的临时丈夫,而是个典型的忘恩负义的负心郎。不但平克顿根本没把痴情的蝴蝶夫人放在眼里,他的美国妻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她在领事馆见到蝴蝶夫人乔乔桑时,她居高临下地说道:“多迷人,多可爱呀!……能亲我一下吗,你这个漂亮的玩物?”
郎的小说对美国人淡淡的讽刺并没有激怒美国读者,向来自高自大不怕人骂的美国读者有足够的肚量来接受这么点批评,或者干脆就没把它看成是批评,相反他们被蝴蝶夫人这个难以想象地温柔恭顺的“理想妻子”迷住了。小说引起了轰动,演艺业的明星、导演、制作人都纷纷来找郎商谈购买舞台剧版权之事。最后郎决定把版权卖给当时美国戏剧界的头号大腕大卫·贝拉斯科。贝拉斯科一身而三任:制作人、编剧、导演,而且都做得极其出色——这样的戏剧全才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过。贝拉斯科和郎合作担任编剧,然后就亲自制作和导演了同名的话剧,于1900年在百老汇推出。按照当时的美学标准和技术条件,这是个极其写实的演出,舞台上所制造的幻觉几可乱真。最为人称道的是一个创纪录的14分钟没有台词的场面,真能让观众以为蝴蝶夫人和她的孩子和佣人在台上挨过了令人心焦的12个小时:角色们等着,看着,夜幕降临了,星星出来了,点了用来欢迎平克顿归来的灯笼一个又一个地熄灭了,台上一片漆黑。然后,渐渐地,东方破晓,鸟儿开始唱起来。14分钟的静场展示了12个小时的生活时间,让贝拉斯科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头的观众都像被魔法镇住了一样。是这个场面确认了这位戏剧家作为“舞台魔法师”的顶级地位,也是这个场面使在伦敦的约克公爵剧院看戏的普契尼最受感动。
普契尼最喜欢这个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听不懂几句英语的台词,但他看懂了这个戏,戏一结束他就走进后台,找贝拉斯科要求买下改编歌剧的版权。
如果觉得《论歌剧《蝴蝶夫人》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